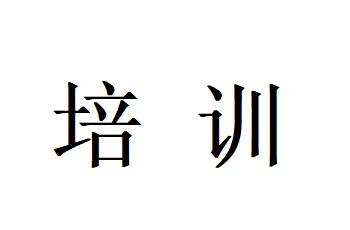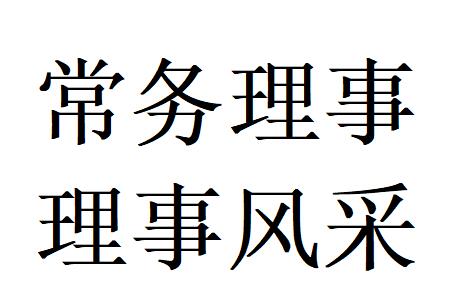期刊杂志
期刊杂志
-
 刊物介绍
刊物介绍
-
 编委会
编委会
-
 《中国有害生物防制》
《中国有害生物防制》
- 《中国有害生物防制》总117期(2025年10月刊)
- 总116期(2025年8月)
- 总115期(2025年6月)
- 总114期(2025年4月)
- 总113期(2025年2月刊)
- 总112期(2024年12月)
- 总111期(2024年10月刊)
- 总110期(2024年8月刊)
- 总109期(2024年6月刊)
- 总108期(2024年4月刊)
- 总107期(2024年2月刊)
- 总106期(2023年12月刊)
- 总105期(2023年10月刊)
- 总104期(2023年8月刊)
- 常务理事、理事风采专栏
- 总103期(2023年6月刊)
- 总102期(2023年4月刊)
- 总101期(2023年2月刊)
- 总100期(2022年12月刊)
- 总99期(2022年10月刊)
- 总98期(2022年8月刊)
- 2021精华合订本
- 总97期(2022年6月刊)
- 总96期(2022年4月刊)
- 2020年精华合订本
- 总95期(2022年2月刊)
- 总94期(2021年12月刊)
- 总93期(2021年10月刊)
- 总92期(2021年8月刊)
- 总91期(2021年6月刊)
- 总90期(2021年4月刊)
- 总89期(2021年2月刊)
- 总88期(2020年12月刊)
- 总87期(2020年10月刊)
- 总86期(2020年8月刊)
- 总85期(2020年6月刊)
- 2019年全年精华合订本(印刷)
- 总84期(2020年4月刊)
- 总83期(2020年2月刊)
- 2019年12月刊
- 2019年10月刊
- 2019年8月刊
- 2019年6月刊
- 2019年4月刊
- 2019年第1期(2月刊)
- 2018年全年精华本(印刷)
- 2018年第5期(12月刊)
- 2018年第4期(10月刊)
- 2018第3期(8月刊)
- 2018年第2期(6月刊)
- 2018年第1期(4月刊)
-
 在线投稿
在线投稿
-
 合作方式
合作方式
-
 《说虫》
《说虫》
- 《说虫》总27期秋冬防鼠灭鼠专刊
- 《说虫》(总26期)
- 《说虫》总25期
- 《说虫》(总24期)
- 《说虫》(总23期)202410
- 《说虫》(第22期)202407
- 《说虫》(第21期 )202401
- 《说虫》(第20期)202311
- 《说虫》(总19期)202308
- 《说虫》总18期(202304)
- 《说虫》总17期(202210)
- 《说虫》(总16期)202208
- 《说虫》202206(总15期)
- 《说虫》202204(总14期)
- 《说虫》202112(总13期)
- 《说虫》202110(总12期)
- 《说虫》202108(总11期)
- 《说虫》202106(总10期)
- 客户刊《说虫》09期202012
- 客户刊《说虫》08期202010
- 客户刊《说虫》07期202008
- 客户刊《说虫》06期(202004)
- 客户刊《说虫》05期(201912)
- 客户刊《说虫》03期(201906)
- 客户刊《说虫》04期(201908)
- 客户刊《说虫》02期(201812)
- 客户刊《说虫》创刊号01期(201806)
总90期(2021年4月刊)
【花开有声】汪诚信:出差五个月,我是名副其实带过枪的人

《滇西纪事》系列
一、 没有用武之地
1958年去云南盈江县出差,实验室在户撒,距缅甸只有十来公里。那时,境外还有国民党残余部队活动,治安不好。当地干部都备有枪支自卫,我们到达后,区政府也一视同仁,给我们发枪。我们外勤组3个人,给了一支步枪,一把手枪。步枪由我们联合工作组的彝族同志背着,手枪归我,配发95颗子弹。在这以前,我看到别人带手枪,很是潇洒、神气,非常羡慕;自己一别,感觉就不一样了。很重,坠着,走快了还压得肚子疼,尤其是下夹和收夹,相当不便。可是,要走家串户工作,没办法,只好别着。几天以后认识到,带枪也有学问。如果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把枪藏在书包里更安全;否则,坏人看你有枪,本来只打算抢钱,也得把你整死;如果为了抢枪,更会把你弄死。最难办的是,坏人脸上没有标志,不好主动出击;等他露出杀机,动手已经晚了。县公安局的人对我们说,你觉得有人很可疑,可以拿枪比着他,把他绑起来,再告诉他,委屈你跟我去区上走一趟;但是,不能把他打死。还好,出差5个月,没有需要自己真正用枪的时候,95颗子弹一颗不缺。虽未用过,我却是名副其实的带过枪的人。
当然,那时的边境,并非太平无事,至少有两件值得一提。其一是,4月30日,区政府通知,国民党残部要入境抢银行,晚上不能外出,不能点灯。每人左臂缠白毛巾,武器要子弹上膛。如果有人进屋,只要左臂没有白毛巾,可以开枪打。我们既紧张又兴奋,熄了灯,坐在蚊帐里等着。晚上九点多钟,听到周围枪声大作,但没有人到我们院子里来。再过一个小时,来了一个带白毛巾的同志,通知,警报解除。这一次,户撒的银行未受损失,但陇川县出了问题。一个银行的女营业员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和匪徒搏斗,被砍去双手。她就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徐学惠。
其二是,我们要到紧靠边境的村寨做试验,为了得到村民的配合,要开群众大会做宣传。白天大家都忙,大会只能在晚上开。这天,我们晚饭后到了现场,但老乡们吃饭很晚,稀稀拉拉到10点多才基本到齐。我正在宣传,忽然看到大门被人踢开,有个区政府的干部闯了进来。他看到我正宣传,一言不发,站在门口。我轻声问:“有事吗?”他回答:“没事。你快讲!”我讲完赶紧出了大门,突然从两侧出来几个小伙子,荷枪实弹,出我意外。再往前走,刚出村寨,路边阴影里又出来十来个人,都背着枪。这时,来人才严肃地说:“你们胆子真大,这是什么地方?区长见你们这时还没回来,命令我们立即出发营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们至此才意识到,太冒失了。还算运气好,他们见到的是人,不是尸。
二、 医院化和车子化
这是一段辛酸的回忆。按当时的认识水平,我们明明知道此事劳而无功,不应该做,但是,为了保护自己,逃避风险,依然毫不犹豫地甚至认真去做。相信有着和我类似遭遇和想法的人为数不少,都应该引以为鉴。显然,这类事情,毛病出在中层以至上层干部身上,他们背离了正确路线,才使我们跟着走弯路,浪费了许多金钱、精力和时光。
1958年出差云南省德宏州,我们小组的任务是做灭鼠试验。当时,强调政治挂帅,打破条条框框,最常见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因此,所有出差组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当地领导布置的中心工作。有一天,当地政府召开大会,在一番动员之后,给每个行动小组的具体任务是:为各自负责的行政村建立一所医院,必须在当天建成,以实现全区医院化。散会时已近上午9时,我和老陈同志是一个小组,接令后岂敢怠慢,立即领来出诊包,到区医院的药房选领药物和器材。好在他学过医,我学过药,准备并不困难,半个小时后便向这个村寨进发。到村后找到农业合作社社长,说明来意,交待任务,社长很快找来一个青年,接受我们的培训。老陈不断地讲授,小伙子不停地点头,我则不停地把各种药的服法和剂量,写在小纸片上,贴到带去的每个药瓶上面。两个小时后,培训结束,我们找来纸、笔,写上医院名称,贴在一座无人居住的房屋大门上,按时完成了区政府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回到驻地汇报后,天还没黑呢。这样办医院,可以说是胡来,但我们倒不担心出事,因为,这个阿昌族青年虽然不停地点头,但一直未做笔记,听懂多少很难说,他认得多少汉字也不了解;其次,我们带去的都是很普通的药,量很少,每种都只够一个患者一两天服用。当然,这所所谓医院的命运是不言自明的,刚开办便必定关门,一个病人没治就收摊了。这样办医院,办这样的医院,是不是荒唐?本来,为边疆兄弟民族解决缺医少药的困难很有必要;但如此草率必定事与愿违,于事无补。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任务当时不接受就对了,何苦去做呢?现在看,当然如此,这样办医院只能劳民伤财;可当时,不去做风险很大,除了会失去当地对我们本职工作的支持以外,当事人还可能被上纲上线,后患无法预料,也许会影响后半生。违心做荒唐事,一个人做是劳民伤财,许多人去做就是很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政策被下面曲解,贯彻走样,实在痛心。
此后不久,还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又接受了实现村村寨寨车子化的任务。当地山陡林密,地形起伏,村民运送物品,非挑即揹,而且所挑箩筐紧靠扁担,吊绳很短,很是奇特。外来人过些日子才会明白,这是适应当地情况的好办法,可以避免在挑担向前行走时撞上陡坡,很实用,祖祖辈辈沿用了许久。1958年,为了提高效率,云南省的平原地区提倡以车载代替肩挑,这本是提高工效的大好事,有积极意义。不幸的是,当时一刀切之风猛吹,云南全省无论山区平原,均需实现车子化,没有例外。命令层层下达,层层加码,直到我们所在的边境村寨,我们也就再次结伴而行,接受当地政府布置的任务,帮助一个村寨实现车子化。与医院化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只需传达命令、监督执行,不必传授技术、供应物品。于是,当地政府一声令下,一天之内,全区家家户户都有了各式各样的车状物。但一缺技术,二缺轴承,这些独轮车的轱辘很难滚动;加上地无三尺平,真正的车子都不好用,何况这些车状物?结局可想而知。此事是不是也很荒唐?
但愿这类荒唐事今后永远不再出现。
(未完待续)

汪诚信 男,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1955年—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1957年—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3年—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研究领域 一直从事传染病的媒介与宿主的生态学与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尤其对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及居民区鼠类的防制有较高造诣。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卫生部评为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1年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0年被卫生部授予三峡库区公共卫生保障先进个人。主要著作有:汪诚信、潘祖安,《灭鼠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汪诚信,《老鼠与鼠害的防制》,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汪诚信,《药物灭鼠》,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汪诚信,《灭鼠技术与策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汪诚信、刘起勇,《家庭防虫灭鼠》,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汪诚信、刘起勇,《家庭卫生害虫趣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汪诚信,《有害生物防治(PCO)手册》,武汉出版社,2002;汪诚信、刘起勇、姜志宽,《有害生物治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汪诚信,《有害生物管理(PMP)手册》,武汉出版社,2006;汪诚信,《汪诚信文辑》(1,2),武汉出版社,2009。
1981年—1989年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2005年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现为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起曾任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主编,现为名誉主编;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