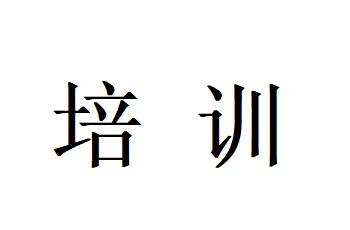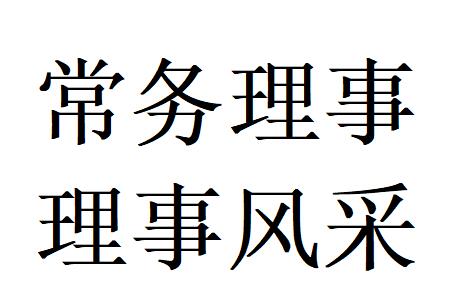期刊杂志
期刊杂志
-
 刊物介绍
刊物介绍
-
 编委会
编委会
-
 《中国有害生物防制》
《中国有害生物防制》
- 《中国有害生物防制》总117期(2025年10月刊)
- 总116期(2025年8月)
- 总115期(2025年6月)
- 总114期(2025年4月)
- 总113期(2025年2月刊)
- 总112期(2024年12月)
- 总111期(2024年10月刊)
- 总110期(2024年8月刊)
- 总109期(2024年6月刊)
- 总108期(2024年4月刊)
- 总107期(2024年2月刊)
- 总106期(2023年12月刊)
- 总105期(2023年10月刊)
- 总104期(2023年8月刊)
- 常务理事、理事风采专栏
- 总103期(2023年6月刊)
- 总102期(2023年4月刊)
- 总101期(2023年2月刊)
- 总100期(2022年12月刊)
- 总99期(2022年10月刊)
- 总98期(2022年8月刊)
- 2021精华合订本
- 总97期(2022年6月刊)
- 总96期(2022年4月刊)
- 2020年精华合订本
- 总95期(2022年2月刊)
- 总94期(2021年12月刊)
- 总93期(2021年10月刊)
- 总92期(2021年8月刊)
- 总91期(2021年6月刊)
- 总90期(2021年4月刊)
- 总89期(2021年2月刊)
- 总88期(2020年12月刊)
- 总87期(2020年10月刊)
- 总86期(2020年8月刊)
- 总85期(2020年6月刊)
- 2019年全年精华合订本(印刷)
- 总84期(2020年4月刊)
- 总83期(2020年2月刊)
- 2019年12月刊
- 2019年10月刊
- 2019年8月刊
- 2019年6月刊
- 2019年4月刊
- 2019年第1期(2月刊)
- 2018年全年精华本(印刷)
- 2018年第5期(12月刊)
- 2018年第4期(10月刊)
- 2018第3期(8月刊)
- 2018年第2期(6月刊)
- 2018年第1期(4月刊)
-
 在线投稿
在线投稿
-
 合作方式
合作方式
-
 《说虫》
《说虫》
- 《说虫》总27期秋冬防鼠灭鼠专刊
- 《说虫》(总26期)
- 《说虫》总25期
- 《说虫》(总24期)
- 《说虫》(总23期)202410
- 《说虫》(第22期)202407
- 《说虫》(第21期 )202401
- 《说虫》(第20期)202311
- 《说虫》(总19期)202308
- 《说虫》总18期(202304)
- 《说虫》总17期(202210)
- 《说虫》(总16期)202208
- 《说虫》202206(总15期)
- 《说虫》202204(总14期)
- 《说虫》202112(总13期)
- 《说虫》202110(总12期)
- 《说虫》202108(总11期)
- 《说虫》202106(总10期)
- 客户刊《说虫》09期202012
- 客户刊《说虫》08期202010
- 客户刊《说虫》07期202008
- 客户刊《说虫》06期(202004)
- 客户刊《说虫》05期(201912)
- 客户刊《说虫》03期(201906)
- 客户刊《说虫》04期(201908)
- 客户刊《说虫》02期(201812)
- 客户刊《说虫》创刊号01期(201806)
总105期(2023年10月刊)
【花开有声】汪诚信:20世界80年代我们出差只能借宿老乡家
六、和老乡同住
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农村出差10天以上,常常要和老乡同住,尤其是在东北和内蒙古。老乡的家不是旅馆,更不是自己的家,又是几个人合住,只能算是特殊的集体宿舍。那时是计划经济,我们出差为公,防病治病搞科研,老乡有义务支持,因此,在老乡家是借住,不付租金。运气好时,借住公社或生产队的房子,由出差组专用。有时,借住老乡的闲房,打扫干净之后专用。记得有一次,我们新到一个农村,到生产队联系住房,生产队队长想了一想,问我们怕不怕鬼?我们大声回答:不怕。结果搬进了一个农家小院,五间正房,有八成新。房子的主人两个月前因故上吊自杀,剩下的家庭成员搬走,小院成了凶宅,谁也不敢住,成全了我们。据说,我们平平安安走后,老乡们不怕了,又有人入住。有时房子紧张,只好和老乡同住一室,主人住南炕,我们住北炕。好在天凉,穿着棉毛衫睡,小心一些就行。不过,我们知道,熄灯后不要用手电筒照对面,有人走动更不能照。因为,不少老乡有光身睡觉的习惯。刚到东北农村出差就听说,有个儿媳妇和公公不和,想报复;晚上她听到公公起夜出去了,马上点起小油灯,纳鞋底。公公方便完了不能回房,站在外面等屋里熄灯,冻得够呛。等了好久灯还亮着,公公只好和儿媳一个房里一个房外吵了起来。第二天还到生产队评理。
房屋最紧张的时候,和老乡睡在同一张炕上,这就更加需要注意,听从主人安排。通常,主人会让客人靠墙睡,男主人挨着客人。有过几次,出差组的男、女同志迫不得已,只能睡在同一张炕上,那就在男、女之间放一个炕桌或箱子,作为边界。
和藏族同胞同住牛毛帐篷又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帐篷里没有炕,没有床,连行军床也没有,席地而卧。藏民保护环境,搭帐篷不除草,直接坐、卧在草地上。有时,帐篷里还有小灌木、小土包。其次,帐篷里有炉灶,烧火时有一点暖意。不过,由于四面通风,中午不如帆布帐篷里面热,晚上却和帐篷外面一样冷。因为,帐篷前面没有门,顶上有天窗,左右和后面的帐篷离地,码了两个柜子和羊皮口袋、石块;加之帐篷是用牦牛毛自己编织的,和麻袋差不多,明亮的月光可以丝丝透入。换句话说,帐篷对于冷空气,基本上不设防,如果说有作用,那就是挡一点风,降低了风速。和藏民同住,就得按他们的习惯,男的住在进门的右侧,头在里面,脚在外面。晚上起夜要小心狗;说来也有意思,当地的狗,责任区概念非常明确:帐篷里面概不负责,一出帐篷,那怕只出来一条腿,它就会管。当然,和它混熟了没问题,否则,它会大叫甚至向你扑来。这时,手电筒很有用,亮光照着它它就不动了,这一点,和狼一样。不过,在出帐篷前,千万不要开手电筒,因为,炉灶很矮,不能挡光,主人睡在那边,直接照射可能伤及隐私。(未完待续)

汪诚信 男,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1955年—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1957年—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3年—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研究领域 一直从事传染病的媒介与宿主的生态学与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尤其对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及居民区鼠类的防制有较高造诣。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卫生部评为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1年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0年被卫生部授予三峡库区公共卫生保障先进个人。主要著作有:汪诚信、潘祖安,《灭鼠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汪诚信,《老鼠与鼠害的防制》,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汪诚信,《药物灭鼠》,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汪诚信,《灭鼠技术与策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汪诚信、刘起勇,《家庭防虫灭鼠》,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汪诚信、刘起勇,《家庭卫生害虫趣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汪诚信,《有害生物防治(PCO)手册》,武汉出版社,2002;汪诚信、刘起勇、姜志宽,《有害生物治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汪诚信,《有害生物管理(PMP)手册》,武汉出版社,2006;汪诚信,《汪诚信文辑》(1,2),武汉出版社,2009。
1981年—1989年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2005年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现为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起曾任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主编,现为名誉主编;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