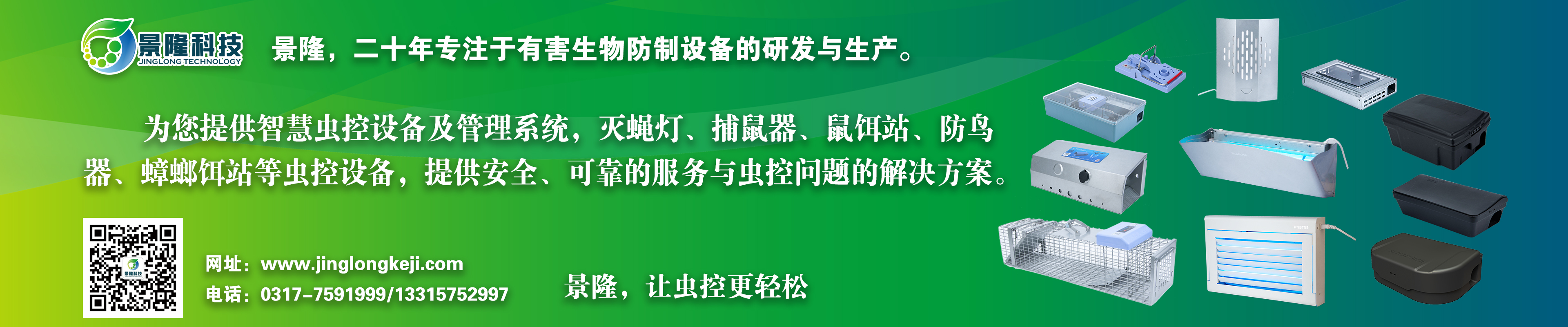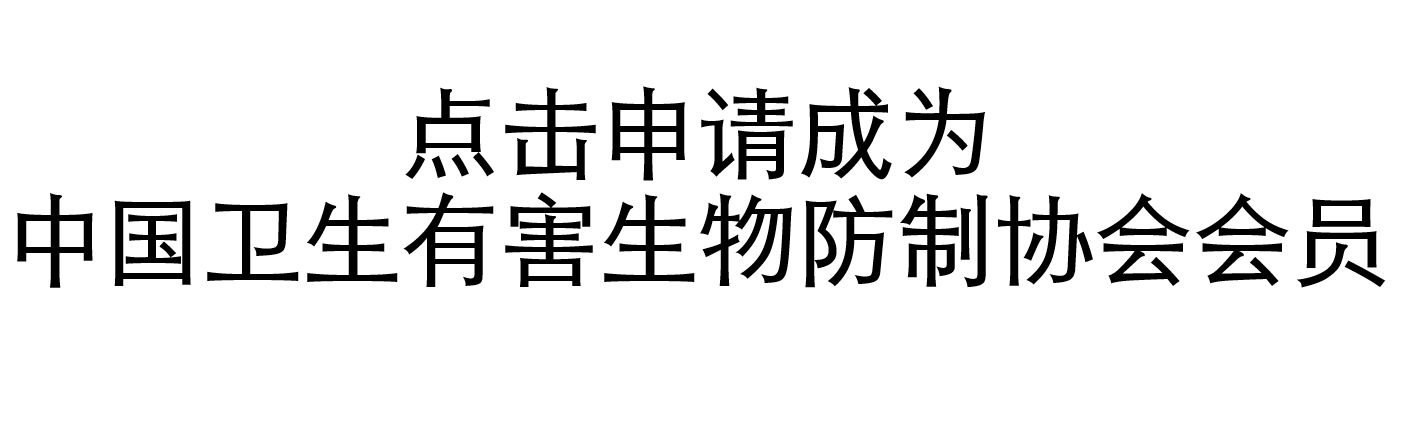期刊杂志
期刊杂志
-
 刊物介绍
刊物介绍
-
 编委会
编委会
-
 《中国有害生物防制》
《中国有害生物防制》
- 总108期(2024年4月刊)
- 总107期(2024年2月刊)
- 总106期(2023年12月刊)
- 总105期(2023年10月刊)
- 总104期(2023年8月刊)
- 常务理事、理事风采专栏
- 总103期(2023年6月刊)
- 总102期(2023年4月刊)
- 总101期(2023年2月刊)
- 总100期(2022年12月刊)
- 总99期(2022年10月刊)
- 总98期(2022年8月刊)
- 2021精华合订本
- 总97期(2022年6月刊)
- 总96期(2022年4月刊)
- 2020年精华合订本
- 总95期(2022年2月刊)
- 总94期(2021年12月刊)
- 总93期(2021年10月刊)
- 总92期(2021年8月刊)
- 总91期(2021年6月刊)
- 总90期(2021年4月刊)
- 总89期(2021年2月刊)
- 总88期(2020年12月刊)
- 总87期(2020年10月刊)
- 总86期(2020年8月刊)
- 总85期(2020年6月刊)
- 2019年全年精华合订本(印刷)
- 总84期(2020年4月刊)
- 总83期(2020年2月刊)
- 2019年12月刊
- 2019年10月刊
- 2019年8月刊
- 2019年6月刊
- 2019年4月刊
- 2019年第1期(2月刊)
- 2018年全年精华本(印刷)
- 2018年第5期(12月刊)
- 2018年第4期(10月刊)
- 2018第3期(8月刊)
- 2018年第2期(6月刊)
- 2018年第1期(4月刊)
-
 《说虫》
《说虫》
- 《说虫》(第21期 )202401
- 《说虫》(第20期)202311
- 《说虫》(总19期)202308
- 《说虫》总18期(202304)
- 《说虫》总17期(202210)
- 《说虫》(总16期)202208
- 《说虫》202206(总15期)
- 《说虫》202204(总14期)
- 《说虫》202112(总13期)
- 《说虫》202110(总12期)
- 《说虫》202108(总11期)
- 《说虫》202106(总10期)
- 客户刊《说虫》09期202012
- 客户刊《说虫》08期202010
- 客户刊《说虫》07期202008
- 客户刊《说虫》06期(202004)
- 客户刊《说虫》05期(201912)
- 客户刊《说虫》03期(201906)
- 客户刊《说虫》04期(201908)
- 客户刊《说虫》02期(201812)
- 客户刊《说虫》创刊号01期(201806)
-
 在线投稿
在线投稿
-
 合作方式
合作方式
总103期(2023年6月刊)
【花开有声】汪诚信:50年代出差 我常担当“找旅馆”的角色
4、跑步找旅店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刚工作不久,由于比较外向,常常担当找旅馆的角色。那时,我的科室主任年青,容易被人低估,当成一般干部,因此,我建议他走在后面,因为他自我介绍不方便,不如我来扮演跟班的角色。于是,我抢先一步到登记处,端起架子,说是给中央鼠疫防治所的主任订房间。特别强调‘中央’和‘主任’两个词。当然,这样炒作的结果是三赢,旅馆好房间卖出去了,我们都有机会住好房间,反正我和他是一根绳上拴的蚂蚱,他住好了,我也有一份。在40岁以前,我腿脚比较麻利,反应也比较快,登记旅馆经常是我的事。
此后不久,我逐渐发现,出差找旅店越来越困难。这主要是因为,人员流动增加得快,而旅店增加慢;尤其是为了各种目的的外调相当多,每项外调都得两人同行,更使旅店供不应求。到改革开放以前,找旅馆可真不容易,尤其是有的出差任务,去的地方是穷乡僻壤,条件差,旅店本来就少;有的出差任务要去的地方多,但每地住的天数少,更难办。下车前就要落实好登记住店的人。为了抢占先机,跑步登记的一般是机灵的年轻人,火车或汽车到站前,他的东西就要交给别人代拿,一下车立刻轻装往旅客登记处跑,争取排在登记队伍的前几名。即使如此,也不见得住得上满意的旅馆。如果一个人出差,就只有人自为战,自己照顾自己了。
回想起来,那时争先恐后地登记旅馆,一是为了能住进正规旅馆,而且尽量住好一点的,万一没有登记上,只能住澡堂,也要矬子里拔大个,找个方便一点的,总之,力争上游。二是尽量找干净的地方住。从卫生方面衡量,一般而言,南方的比北方的卫生,大城市的比中小城市的干净;到了公社、乡镇,那就不抱幻想,碰运气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的地方的小旅店、小客栈相当脏,被褥黑亮还有汗味,我们只好横着盖或翻着盖,或者不脱衣服睡。如果被褥既脏又有虱子,那就让我们左右为难:穿着衣服睡吧,脏的问题小些,但虱子肯定钻到内衣里去;脱个精光睡呢,虱子不上身,却要和脏被褥零距离接触,相当腻歪。比较起来,澡堂里别的条件差,虱子倒比旅店少些。
除了卫生问题,还遇到过一些稀奇事情。
20世纪70年代末又去云南,在大理市住招待所。招待所主楼共四层,有近200间客房,每间房住4人。房间不坏,设备一般,行李干净,但必须到楼外很大、很干净的公共厕所方便。更绝的是,旅馆服务员每到晚上8点,不厌其烦地把每间房里的脸盆收走,防止客人用它方便。因此,晚上8点以后回招待所,洗脸还要去领盆、还盆。设计者以为,双管齐下可以保证楼内卫生,岂知事与愿违,事实上,每层楼梯的拐角处都有浓浓的尿骚味儿。本来嘛,大家要的是方便,可是夜间出楼上厕所很不方便,那怎么办?只能在楼梯拐角处解决了。有的客人报复的办法更离谱,以至在有的房间里,常能看到茶杯被放在最高一层的窗户格子上,不了解底细的人,包括服务员,一动茶杯准上当。原来,里面装满了尿,端不平必然往外洒,虽然不算倾盆大雨,洒上几点也够呛。
20世纪70年代初,有一年冬天我单独去西安,很幸运登记上旅馆。按当时规定,除非是高级宾馆或特殊场所,西安冬天不供暖。所以,进了旅馆登记时,服务台问我要几床被,我摸不着头脑,只好说别人几床我也几床,结果是人人都是三床,我虽然莫名其妙,也要了三床。那时客房里没有电视,晚上大街上冷冷清清,除了看“老三战”等电影,无事可做,只能早早上床。天冷尿多,还没有入睡就要上厕所。偏偏厕所在后院,距离将近80米,一个来回,睡意全无。被子再多也无济于事,刚睡暖又要起夜,一个晚上折腾了四次。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旅店好找,卫生的问题已经逐渐解决,但从南到北,新问题又来了。晚上9、10点钟,我刚要入睡,电话铃响,拿起一听,里面娇声娇气地问:“先生,您要按摩吗?”虽然我客客气气而又坚定地回答:“不要,谢谢。”半个小时左右,刚刚睡着,电话又响。接,还是不接?不接,怎么知道是否真的有工作联系?接,还是按摩小姐在说话。一气之下,睡意全消。幸亏经过不断地整顿,这股歪风终于停息。
关于旅馆,我在蚌埠住过最大的房间,是大礼堂或食堂改的,有96张床,每四张固定在一起,自己携带的物品一概放在床板底下,万无一失。而且,彻夜开灯,晚上梦话等什么声音时有所闻,很是热闹。这个旅馆房间之大,对我个人来说,算是吉尼斯世界记录,迄今没有打破,料想以后更不会打破。
还听到过有关住店的趣事。20世纪7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提高革命性,单位时兴改名。据朋友说,某地防疫系统几个单位并到一起,合称防疫大队,用一个公章。不料这么一改,出差找旅馆出了问题。旅馆登记处一看介绍信上的公章,立刻退了过来,说:“大队的介绍信不行,要公社的。”向他解释:“我们是防疫大队。”“什么大队都不行,级别都一样。”他把“防疫”当成大队的名字了。
(未完待续)

汪诚信 男,195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药化系。1955年—1957年长春鼠疫防治所,药师;1957年—198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3年—1999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研究领域 一直从事传染病的媒介与宿主的生态学与防治方法、策略的研究,尤其对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的宿主及居民区鼠类的防制有较高造诣。1986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卫生部评为救灾防病先进个人;1991年领取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中国科协优秀建议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2010年被卫生部授予三峡库区公共卫生保障先进个人。主要著作有:汪诚信、潘祖安,《灭鼠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汪诚信,《老鼠与鼠害的防制》,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汪诚信,《药物灭鼠》,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汪诚信,《灭鼠技术与策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汪诚信、刘起勇,《家庭防虫灭鼠》,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汪诚信、刘起勇,《家庭卫生害虫趣谈》,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汪诚信,《有害生物防治(PCO)手册》,武汉出版社,2002;汪诚信、刘起勇、姜志宽,《有害生物治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汪诚信,《有害生物管理(PMP)手册》,武汉出版社,2006;汪诚信,《汪诚信文辑》(1,2),武汉出版社,2009。
1981年—1989年曾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2005年曾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主任委员,现为名誉主任委员;1992年起曾任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副会长、顾问;曾任中国植物保护学会鼠害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自然疫源性疾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主编,现为名誉主编;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